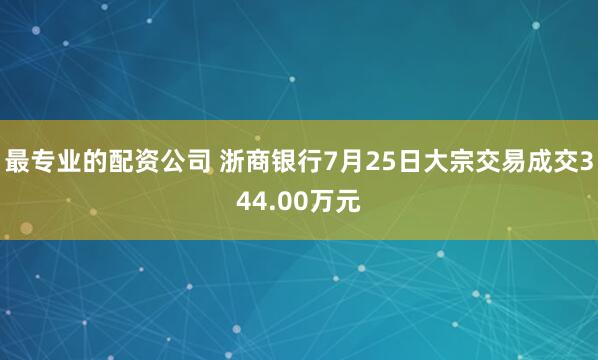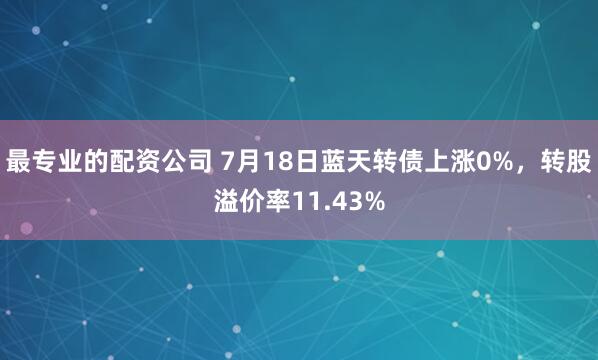“阿曾,你怎么不来看我?”1953年3月的一天最专业的配资公司,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突然停下脚步,冲着人群里的曾宪植发了一句半嗔半笑的责问。这声乡音不高,却让走廊里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。曾宪植立刻站直,回敬一句同样的湘味儿:“主席,我怕打扰您哩!”一句话,尴尬化开,空气里多了几分暖意。

彼时,距开国大典已经过去三年。曾宪植的身份,在座的人都知道:中央妇联副秘书长、统战老手、革命功臣;但毛主席这一声“阿曾”,却把她拉回了更早的岁月——那个篮球场上短发飘扬、弹指间投篮百发百中的湖南姑娘。许多人都好奇,何以一位妇女干部能让毛主席如此亲切?要回答这个疑问,得把时间拨回到1910年。
1910年初夏,湘乡曾家老宅里传来婴儿啼声。家族谱牒上,她被记下名讳——曾宪植。曾家乃曾国藩一脉,积淀深厚。屋檐上的翘角、厅堂里的牌匾,都在提醒来客:这里出过封疆大吏。名门出闺秀,本是寻常戏码,可这位闺秀的台词写得极不寻常。
六岁进长沙古稻田师范附小,十三岁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。掌校人徐特立开口闭口谈“新思想”,课堂里处处碰撞火花。京剧里,她上台扮包公,黑脸一抹毫不扭捏;操场上,她是全国首支女子篮球队的主力中锋,高吊球弧线优雅。徐特立看她三分欣赏、七分好奇:“女孩子这身板、这心气,将来不甘只在闺阁写诗。”这句话被学生私下传为预言。

1926年秋,武汉街头张贴出一行大字——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公开招收女学员”。社会舆论一片哗然,连《大公报》都说“骇人听闻”。曾宪植拿着招生简章给父亲看,老人沉默片刻,只说:“从前我们曾家靠行伍立功名,若你要走这条路,去吧。”于是,她剪去长辫,独自赴汉。同期报考者数百,最终录取一百九十五,曾宪植行列居前。入校笔试,她写下《关于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》,字字犀利,阅卷官批注:“立意高远,难得女中俊杰。”
训练场上,刺刀操一遍又一遍。学员连长笑说:“名门大小姐能吃这种苦,稀罕!”她淡淡回应:“打仗不认出身。”这股子硬气,很快传遍黄埔系统,连远在广州的蒋校长也点名表扬。

学业未及完成,1927年“四一二”事变骤起,武汉分校被迫停办。女学员们提前编入教导团,赴南下前线。广州起义打响,曾宪植担任准尉文书,统筹伤员转运。也是在这时,她与作战指挥之一的叶剑英相识。第一次见面,叶剑英笑问:“你就是徐老先生口里的投篮高手?”一句调侃拉近了距离,也开启一段情缘。1928年春节前,两人简单举行婚礼,她成了叶夫人,也是新党员。组织随即安排两人留学苏联,可名额临时骤减。曾宪植轻声道:“你去,我留下。”叶剑英无言,终只身赴莫斯科。
留在国内的她,命途继续波折。国民党特务盯上她,逮捕、越狱、再逮捕,连环上演。为避追捕,她短暂赴日求学,却又因“长得太出挑”被当局盯上。审讯时,翻译自称熟读曾国藩家书,她冷冷抛出一句:“我是曾国荃五世孙女。”对方神色大变,日警登时赔笑放人。这段离奇插曲,让她明白老祖先的名声有时能救命,但脚下路仍要靠自己。
1931年冬,她奉命转往香港,夫妻不得不分头行动。几年里,奔走于南粤、桂港之间,掩护情报线。1938年武汉会师,两人才短暂团聚,随后再分离。那年,她生下儿子叶选宁,孩子没来得及喊一声“爸爸”,父亲已负使命离去。1941年春,她被调延安,路上获悉叶剑英重新组建了家庭。信件里,她只写了十二字:“知悉,无碍,望保重革命事业。”平静得像一份工作简报。

1949年10月1日,她随宋庆龄、蔡畅等人登上天安门城楼。礼炮声震耳,她泪如泉涌。宋庆龄拍了拍她手:“阿曾,我们走到今天不易。”她用力点头,语调却依旧平稳:“是胜利,也是新的出发。”当天无数摄影机对准城楼,她站在周总理左侧,鲜有人识得这位“校花女兵”。
建国后,她主抓妇联组织建设。1952年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备期间,毛主席到会,远远便认出她。他故意拉长音调:“这不是阿……阿……阿曾吗?”会场笑声一片。毛主席随后调侃:“你们这支娘子军打得过文正公湘军不?”她立正答:“打得过,肯定打得过!”一句干脆,底气十足。

三年后,便有了开头那场走廊重逢。毛主席拧眉质问,她轻声解释。简单几句寒暄,既是首长关怀,也是同乡旧友的惦念。外人看得新鲜,她却清楚:那份关注来自共同的湖南血脉,更来自几十年风雨互相托付的革命感情。
进入六十年代,曾宪植也未能完全幸免政治风浪。一度被审查,生活窘迫。周总理遵主席口示,悄悄为她安排住所、送去医药。低谷时期她只说一句:“日子能苦,志气不能塌。”1978年,政策拨乱反正,她恢复职务,出任全国妇联副主席。1982年离休后,她定居澳门,仍关注内地妇女事业。1989年暮春,她静静离世,终年七十九岁。
说到她与叶剑英唯一的儿子叶选宁,命途同样多舛。少年进京,与父团聚,却在渤海湾劳动时右臂被机器绞断。医护连夜抢救,周总理亲自批示留住这只断臂。后来,他靠左手苦练书法,最终成为军界知名的单臂书家,这份韧劲,与母亲如出一辙。

曾宪植这一生,起点是深宅大院,落点是共和国将星与元勋之间的交汇处。她没将青春留给闺房,而是留给了战火、监牢、会场、文件堆与无数素未谋面的妇女同胞。有人感叹她的婚姻缺憾,她自己却用行动回答:个人得失很小,时代命题更大。或许,1953年那一句“阿曾,你怎么不来看我”,恰恰说明她早已被写进了新中国的集体记忆,位置虽低调,却牢不可破。
宝尚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